張信鴻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現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他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場論、統計物理、量子場論、弦理論等,特別是在非平衡統計物理和冷原子物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張信鴻教授於1963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198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91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隨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等多個知名學府擔任過研究員和教授。
張信鴻教授的學術貢獻不僅在理論物理領域有所建樹,在科學傳播和科學教育方面也十分活躍,他的著作《無所不在的平衡》被譽為物理學普及的經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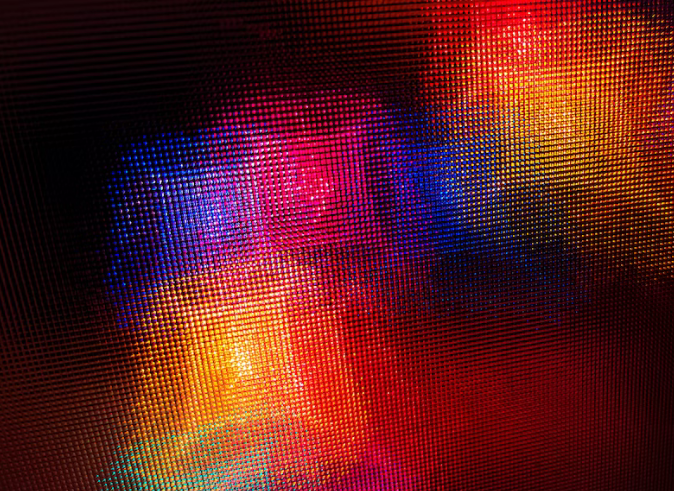
20世紀的前30年,是物理開展大迸發的年代。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相繼提出,大大改動了物理學的相貌,使得人們關於時空、因果律、隨機性的見地都發作了基本的改動。
從20世紀前半到如今,固態物理、高能物理、半導體物理、光電科技、納米科技,與能源科技的開展,以及正在如火如荼開展中的量子資訊科技,或多或少都牽涉到量子力學的應用。而核能科技、宇宙學研討、重力波偵測、科幻電影(例如《星際效應》)中關於黑洞與蟲洞(blackhole and wormhole)的物理特性模仿,以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全球定位係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都可算是相對論的應用。
生活在這樣一個高科技的時期,再加上許多名人關於新物理的鉅大成就的普遍宣傳,普通人或許會逐步置信新物理曾經完整取代了舊物理,因而不需求學習已被淘汰的舊物理,只需學習新的就好。在一些內容牽扯到相對論或量子力學的YouTube視頻(它們一定是科普視頻)裏,常常有“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力學”的說法。在一些上世紀的科普書裏,相似的敘說也很常見。但是,這樣的說法終究對不對呢?
在答復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首先比擬一下新舊理論,對同一個物理現象的數據描繪有多大的差別,以及這個差別能否重要。
以牛頓力學跟狹義相對論比擬,固然他們給出的時空觀很不一樣,物理公式的容貌也有許多差別,但它們在物體的運動速度v遠小於光速c時,對同一個物理量會給出簡直一樣的結果,差異僅在(v/c)2 的等級。假定我們追求的準確度請求這個偏向在百萬分之一(10−6)以下,那麼在速度 v ⩽0.001c ≈300km/s 以下時,都沒有必要運用相對論。這個速度上限大約是900馬赫,遠遠超越人類飛行器、流星,與太陽係內星體的運動速度。
因而,除非是對準確度有更高的請求,或是誤差會隨時間不時纍積(例如GPS、水星軌道的近日點進動),或是此差別因乘上某些宏大的係數(例如庫倫常數)而成爲另一種可觀測的物理量,否則是不用思索相對論的。
事實上,磁力作爲靜電力的相對論效應就是後一種狀況:一個截面積1mm2 的銅製導線中若經過10Amp電流,對應的電荷漂移速度其實只要0.6mm/s,但磁力的存在卻是很顯而易見的。這或許是最令人印象深入的低速相對論效應了。除了以上所提到的這幾種狀況外,在處置其它低速物體運動相關的物理現象時,相對論並不需求被認真思索。
將牛頓力學跟量子力學相比就更有趣了。依據量子力學,物體的位置與動量各有一個不肯定度(uncertainty),它們的乘積大約等於普朗克常數(Planck’s constant)。關於原子中的電子而言,位置的不肯定度與其物質波(matter wave)的波長同等級,而這個尺度恰恰大約是原子的大小。

所以,若採用波模態(wave modes)的觀念,並配合能量與頻率的正比關係 E=hν=ℏω,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由薛丁格方程式解出的電子軌域(electron orbital)型態。
關於一個像地球這麼大質量的物體,它的位置不肯定度有多大呢?依據天文學的材料,地球質量大約是M地球=5.97×1024kg,而它繞行太陽的速度大約是 v地球=3×104m/s,所以相關於太陽的動量是 p地球=1.8×1029kg⋅m/s。代入物質波的波長公式 λ=h/p 就得到 λ地球=3.7×10−63m=3.7×10−54nm。
前面說過,位置的不肯定度跟物質波波長在同一等級,所以因量子力學緣由而招致的地球位置的不肯定度,就是10−54nm 的等級,而這是一個人類科技到目前爲止基本不可能量到的長度!假如把地球的運動軌跡由一條數學上的理想麯線,換成一根粗細等於位置不肯定度的管子,那麼由於這根管子真實太細了,所以它與理想的麯線的區別在實踐的觀測中是顯現不出來的。因而,在星體運動的問題上,沒有思索量子力學描繪的必要性。
讀者或許會覺得星體的質量太大了,不用運用量子力學是很顯然的。爲了進一步探求牛頓力學的適用範圍,讓我們思索一個直徑1微米(1μm)的水滴,以每秒1公分(1cm/s)的速度挪動。根因而數據可計算出水滴的動量是 p=5.24×10−18m/s,對應的物質波波長爲 λ=1.3×10−16m=1.3×10−7nm,遠小於水滴直徑,因而其位置不肯定度也是遠小於此水滴直徑與途徑尺度。
所以,大至星體,小至微米尺度的小顆粒,當我們討論的只是它們的運動問題時,是不需求運用量子力學的。不過,若研討的是這個微米水滴的外表張力,或是它的化學性質,量子力學通常就需求被思索。
從以上這些簡單的預算能夠看出來,固然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是現代物理的兩大基石,是根本物理定律必需契合的框架,但並不是運用了它們就一定能夠更好的幫我們處理問題,或理解物理現象的細節。很多時分它們對問題的處理沒有本質協助,卻要消耗更多的計算資源。
假如把相對論與量子力學這兩個理論比喻爲“牛刀”,那麼物理學家通常在處理問題時,並不會直接運用這兩把牛刀,而是靈敏地運用各種較笨重好用的工具刀,再看看能否有需求加上來自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小幅度修正。那些需求思索的修正通常會以某種“修正項”的型態,分離到舊理論的框架裏,而協助我們更好的處理問題。

回到關於牛頓力學能否已被推翻的問題。經過以上的解釋,置信讀者都已理解:新舊理論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拆掉老舊的房子,蓋起一棟新大樓,從此不再與老房子有關。我以爲它們更像是精細水平不同的工具,能夠視狀況交換運用。當處置某些問題,並不需求極高的精細度時,我們就能夠運用較粗糙但是便當運用的舊工具,而不是非用新的不可。
以這種意義而言,牛頓力學並不是被推翻了,而是我們關於它的適用範圍有了更分明的認識。能夠預期,未來會呈現新理論取代相對論與量子力學,那時我們就會曉得它們的運用範圍要遭到什麼限製。
有些時分,人們以至會暫時犧牲新理論的某些普遍性,並讓它與舊理論的方程式相分離,以建構出某種好用的模型。例如在電漿光子學(plasmonics)與超穎資料(metamaterials)研討中,常被運用的Drude模型(Drude model),就是應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計算電荷在電磁場作用下的運動,並根因而運動計算出極化電流(polarization current),再代入馬克斯威方程組中,就能夠十分好的解釋光在金屬與超穎資料中的傳播行爲。
在這種做法中,馬克斯威方程組所描繪的電磁場能否具有相對論所請求的羅倫茲協變性(Lorentz invariance),是沒有思索的。這是由於在這個模型適用的場所中,電荷的挪動速度都是遠小於光速的,所以沒有必要爲了追求羅倫茲協變性而讓模型過度的復雜化。研討者只在意如何在 “介質參考係” 中處置問題,而把如何將理論擴展成具有羅倫茲協變性的問題留給未來。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標題:張信鴻教授|解讀牛頓力學的新舊理論
地址:https://www.twetclubs.com/post/6401.html






